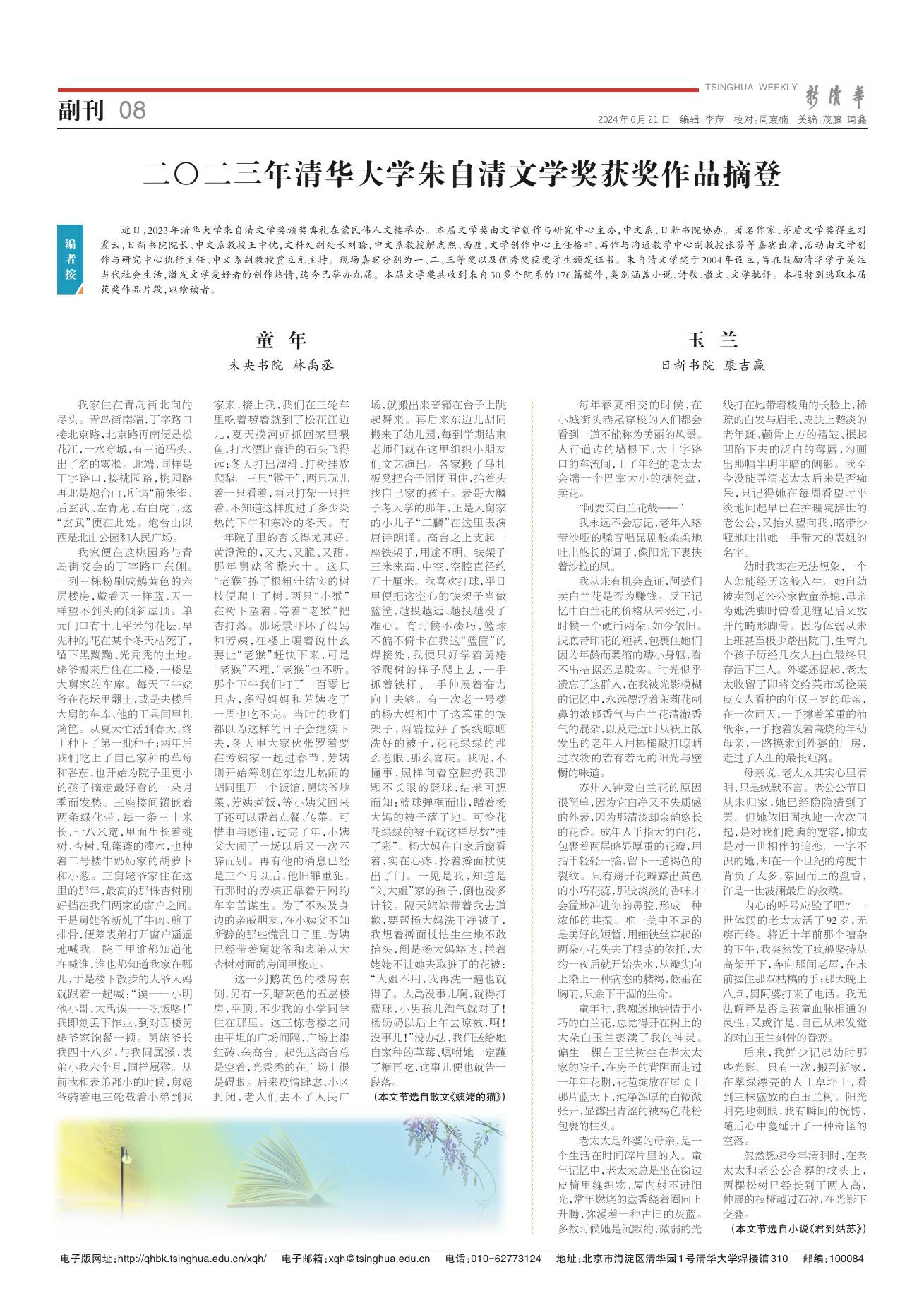二〇二三年清华大学朱自清文学奖获奖作品摘登
新清华 2024年06月21日 第2331期 副刊
编者按
近日,2023年清华大学朱自清文学奖颁奖典礼在蒙民伟人文楼举办。本届文学奖由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办,中文系、日新书院协办。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日新书院院长、中文系教授王中忱,文科处副处长刘晗,中文系教授解志熙、西渡,文学创作中心主任格非,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副教授张芬等嘉宾出席,活动由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文系副教授贾立元主持。现场嘉宾分别为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奖获奖学生颁发证书。朱自清文学奖于2004年设立,旨在鼓励清华学子关注当代社会生活,激发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迄今已举办九届。本届文学奖共收到来自30多个院系的176篇稿件,类别涵盖小说、诗歌、散文、文学批评。本报特别选取本届获奖作品片段,以飨读者。
童 年
未央书院 林禹丞
我家住在青岛街北向的尽头。青岛街南端,丁字路口接北京路,北京路再南便是松花江,一水穿城,有三道码头、出了名的雾凇。北端,同样是丁字路口,接桃园路,桃园路再北是炮台山,所谓“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这“玄武”便在此处。炮台山以西是北山公园和人民广场。
我家便在这桃园路与青岛街交会的丁字路口东侧。一列三栋粉刷成鹅黄色的六层楼房,戴着天一样蓝、天一样望不到头的倾斜屋顶。单元门口有十几平米的花坛,早先种的花在某个冬天枯死了,留下黑黝黝、光秃秃的土地。姥爷搬来后住在二楼,一楼是大舅家的车库。每天下午姥爷在花坛里翻土,或是去楼后大舅的车库、他的工具间里扎篱笆。从夏天忙活到春天,终于种下了第一批种子;两年后我们吃上了自己家种的草莓和番茄,也开始为院子里更小的孩子摘走最好看的一朵月季而发愁。三座楼间镶嵌着两条绿化带,每一条三十米长,七八米宽,里面生长着桃树、杏树、乱蓬蓬的灌木,也种着二号楼牛奶奶家的胡萝卜和小葱。三舅姥爷家住在这里的那年,最高的那株杏树刚好挡在我们两家的窗户之间。于是舅姥爷新炖了牛肉、煎了排骨,便差表弟打开窗户遥遥地喊我。院子里谁都知道他在喊谁,谁也都知道我家在哪儿,于是楼下散步的大爷大妈就跟着一起喊:“诶——小明他小哥,大禹诶——吃饭咯!”我即刻丢下作业,到对面楼舅姥爷家饱餐一顿。舅姥爷长我四十八岁,与我同属猴,表弟小我六个月,同样属猴。从前我和表弟都小的时候,舅姥爷骑着电三轮载着小弟到我家来,接上我,我们在三轮车里吃着唠着就到了松花江边儿,夏天摸河虾抓回家里喂鱼,打水漂比赛谁的石头飞得远;冬天打出溜滑、打树挂放爬犁。三只“猴子”,两只玩儿着一只看着,两只打架一只拦着,不知道这样度过了多少炎热的下午和寒冷的冬天。有一年院子里的杏长得尤其好,黄澄澄的,又大、又脆、又甜,那年舅姥爷整六十。这只“老猴”拣了根粗壮结实的树枝便爬上了树,两只“小猴”在树下望着,等着“老猴”把杏打落。那场景吓坏了妈妈和芳姨,在楼上嚷着说什么要让“老猴”赶快下来,可是“老猴”不理,“老猴”也不听。
那个下午我们打了一百零七只杏,多得妈妈和芳姨吃了一周也吃不完。当时的我们都以为这样的日子会继续下去,冬天里大家伙张罗着要在芳姨家一起过春节,芳姨则开始筹划在东边儿热闹的胡同里开一个饭馆,舅姥爷炒菜、芳姨煮饭,等小姨父回来了还可以帮着点餐、传菜。可惜事与愿违,过完了年,小姨父大闹了一场以后又一次不辞而别。再有他的消息已经是三个月以后,他旧罪重犯,而那时的芳姨正靠着开网约车辛苦谋生。为了不殃及身边的亲戚朋友,在小姨父不知所踪的那些慌乱日子里,芳姨已经带着舅姥爷和表弟从大杏树对面的房间里搬走。
这一列鹅黄色的楼房东侧,另有一列暗灰色的五层楼房,平顶,不少我的小学同学住在那里。这三栋老楼之间由平坦的广场间隔,广场上漆红砖、垒高台。起先这高台总是空着,光秃秃的在广场上很是碍眼。后来疫情肆虐、小区封闭,老人们去不了人民广场,就搬出来音箱在台子上跳起舞来。再后来东边儿胡同搬来了幼儿园,每到学期结束老师们就在这里组织小朋友们文艺演出。各家搬了马扎板凳把台子团团围住,抬着头找自己家的孩子。表哥大麟子考大学的那年,正是大舅家的小儿子“二麟”在这里表演唐诗朗诵。高台之上支起一座铁架子,用途不明。铁架子三米来高,中空,空腔直径约五十厘米。我喜欢打球,平日里便把这空心的铁架子当做篮筐,越投越远、越投越没了准心。有时候不凑巧,篮球不偏不倚卡在我这“篮筐”的焊接处,我便只好学着舅姥爷爬树的样子爬上去,一手抓着铁杆、一手伸展着奋力向上去够。有一次老一号楼的杨大妈相中了这笨重的铁架子,两端拉好了铁线晾晒洗好的被子,花花绿绿的那么惹眼、那么喜庆。我呢,不懂事,照样向着空腔扔我那颗不长眼的篮球,结果可想而知:篮球弹框而出,蹭着杨大妈的被子落了地。可怜花花绿绿的被子就这样尽数“挂了彩”。杨大妈在自家后窗看着,实在心疼,拎着擀面杖便出了门。一见是我,知道是“刘大姐”家的孩子,倒也没多计较。隔天姥姥带着我去道歉,要帮杨大妈洗干净被子,我想着擀面杖怯生生地不敢抬头,倒是杨大妈豁达,拦着姥姥不让她去取脏了的花被:“大姐不用,我再洗一遍也就
得了。大禹没事儿啊,就得打篮球,小男孩儿淘气就对了!杨奶奶以后上午去晾被,啊!没事儿!”没办法,我们送给她自家种的草莓、嘱咐她一定蘸了糖再吃,这事儿便也就告一段落。
(本文节选自散文《姨姥的猫》)
玉 兰
日新书院 康吉赢
每年春夏相交的时候,在小城街头巷尾穿梭的人们都会看到一道不能称为美丽的风景。人行道边的墙根下、大十字路口的车流间,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会端一个巴掌大小的搪瓷盘,卖花。
“阿要买白兰花哉——”
我永远不会忘记,老年人略带沙哑的嗓音唱昆剧般柔柔地吐出悠长的调子,像阳光下裹挟着沙粒的风。
我从未有机会查证,阿婆们卖白兰花是否为赚钱。反正记忆中白兰花的价格从未涨过,小时候一个硬币两朵,如今依旧。浅底带印花的短袄,包裹住她们因为年龄而萎缩的矮小身躯,看不出拮据还是殷实。时光似乎遗忘了这群人,在我被光影模糊的记忆中,永远漂浮着茉莉花刺鼻的浓郁香气与白兰花清澈香气的混杂,以及走近时从袄上散发出的老年人用棒槌敲打晾晒过衣物的若有若无的阳光与壁橱的味道。
苏州人钟爱白兰花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白净又不失质感的外表,因为那清淡却余韵悠长的花香。成年人手指大的白花,包裹着两层略显厚重的花瓣,用指甲轻轻一掐,留下一道褐色的裂纹。只有掰开花瓣露出黄色的小巧花蕊,那股淡淡的香味才会猛地冲进你的鼻腔,形成一种浓郁的共振。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美好的短暂,用细铁丝穿起的两朵小花失去了根茎的依托,大约一夜后就开始失水,从瓣尖向上染上一种病态的赭褐,低垂在胸前,只余下干涸的生命。
童年时,我痴迷地钟情于小巧的白兰花,总觉得开在树上的大朵白玉兰亵渎了我的神灵。偏生一棵白玉兰树生在老太太家的院子,在房子的背阴面走过一年年花期,花苞绽放在屋顶上那片蓝天下,纯净浑厚的白微微张开,显露出青涩的被褐色花粉包裹的柱头。
老太太是外婆的母亲,是一个生活在时间碎片里的人。童年记忆中,老太太总是坐在窗边皮椅里缝织物,屋内射不进阳光,常年燃烧的盘香绕着圈向上升腾,弥漫着一种古旧的灰蓝。多数时候她是沉默的,微弱的光线打在她带着棱角的长脸上,稀疏的白发与眉毛、皮肤上黯淡的老年斑、颧骨上方的褶皱、抿起凹陷下去的泛白的薄唇,勾画出那幅半明半暗的侧影。我至今没能弄清老太太后来是否痴呆,只记得她在每周看望时平淡地问起早已在护理院辞世的老公公,又抬头望向我,略带沙哑地吐出她一手带大的表姐的名字。
幼时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人怎能经历这般人生。她自幼被卖到老公公家做童养媳,母亲为她洗脚时曾看见缠足后又放开的畸形脚骨。因为体弱从未上班甚至极少踏出院门,生育九个孩子历经几次大出血最终只存活下三人。外婆还提起,老太太收留了即将交给菜市场捡菜皮女人看护的年仅三岁的母亲,在一次雨天,一手撑着笨重的油纸伞,一手抱着发着高烧的年幼母亲,一路摸索到外婆的厂房,走过了人生的最长距离。
母亲说,老太太其实心里清明,只是缄默不言。老公公节日从未归家,她已经隐隐猜到了罢。但她依旧固执地一次次问起,是对我们隐瞒的宽容,抑或是对一世相伴的追恋。一字不识的她,却在一个世纪的跨度中背负了太多,萦回而上的盘香,许是一世波澜最后的救赎。
内心的呼号应验了吧?一世体弱的老太太活了92岁,无疾而终。将近十年前那个嘈杂的下午,我突然发了疯般坚持从高架开下,奔向那间老屋,在床前握住那双枯槁的手;那天晚上八点,舅阿婆打来了电话。我无法解释是否是孩童血脉相通的灵性,又或许是,自己从未发觉的对白玉兰刻骨的眷恋。
后来,我鲜少记起幼时那些光影。只有一次,搬到新家,在翠绿漂亮的人工草坪上,看到三株盛放的白玉兰树。阳光明亮地刺眼,我有瞬间的恍惚,随后心中蔓延开了一种奇怪的空落。
忽然想起今年清明时,在老太太和老公公合葬的坟头上,两棵松树已经长到了两人高,伸展的枝桠越过石碑,在光影下交叠。
(本文节选自小说《君到姑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