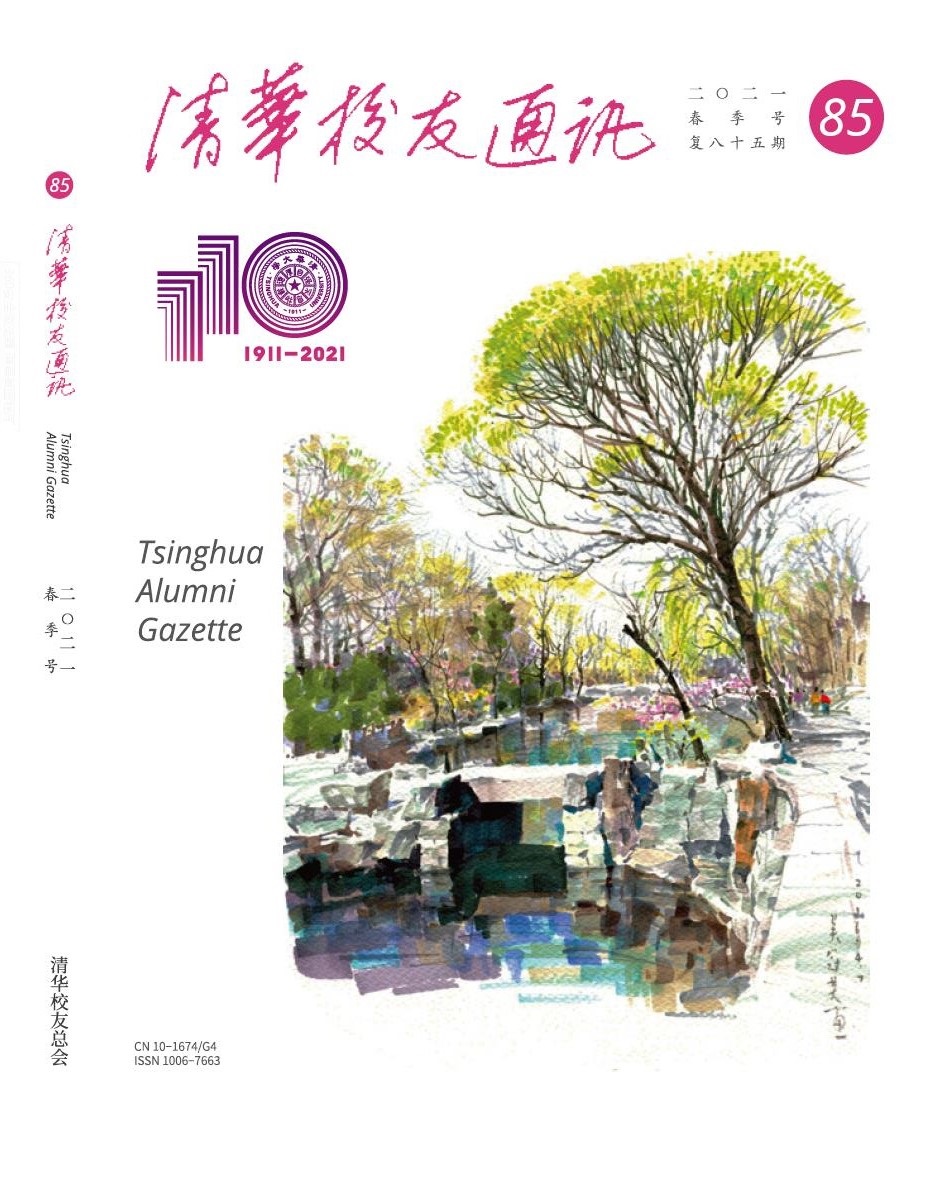南山南(散文节选)
新清华 2025年11月14日 第2382期 副刊
●日新书院 周广臻
人的故乡好像不是出生就有的。至少对于我来说,不是。
你好像需要到外地去,做个异客,且不说漂泊。
那时你再看,看身后,看前方,看头顶,看脚下,然后好像就在一瞬间,故乡就那么地被你看见了。它就在那里。
你还看见了自己。
“南山南,北海北,那里有我的故乡……”
爸妈
“走,我们出去吃饭。”爸说。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天。
今天太阳落得格外的慢,突然想到再看到就是新的一年了,不由得回头多看了两眼。
爸和妈聊单位的事,我和妹玩说颜色猜景物的游戏。我们走了很远、很久,街上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夕阳很温柔地打在背上,下班赶着回家的、奔赴聚会的,还有像我们这样闲逛的。车也多了起来。
人往一边攒动,挤挤囔囔的,都走到了个大广场,突然一下往四处散开。原来是东门啊。妹估计是没有记忆,因为我记忆中都是好小的时候来的。来这里看木偶剧,在一个有点老的、地板砖是橙色的麦当劳里,用十五根吸管连起来喝放在地上的橘子汽水。
旋转自助小火锅,35块钱一个人,有荤有素。老板娘写了张排号单就塞我们手里,爸、我和妹欢天喜地走路带点小跑地进去了,觉得肯定能吃回本。妈最后也进来了。
爸把粉条嗦出很香的声音,辣油滑下来掉在碗里,几滴溅在桌上。妹把浸透了番茄汤的鱼片往小嘴一个劲地塞,咬得糯糯的,再顺一口汤汁下肚。妈也吃,最后还从爸锅里夹了块肉走。我们几个都笑。
汤汁逐渐见底了。几个人扶墙走出店时,看老板娘正往另一家四口手里塞排号单,奶奶牵着蹦跶着的眼巴巴的小孙女,跟着爸爸妈妈往里走。
记忆好像是个很奇怪的东西。这年的最后一晚好像已经是两年半前了。你要我真的去回想,其实这晚的菜并没有那么好吃。杯子接的雪碧是冒牌的勾兑饮料,喝起来像酸甜的水。妹后来跟我说,那鱼有点腥,怪怪的。
可是,现在想想,那晚的菜,怎么就那么好吃呢。
北屋村
那年最后一天,在深圳,我们一家四个就那么走着,把天一点点走黑了。经过小时候住的北屋村时,只剩下挨着马路的两栋了。后面的已经看不到楼了,应该都已经倒了下去,这么一纵地倒下去,一直倒到笔架山的脚下。下面埋着的是我的十年。
6块钱一份的蛋肉肠粉,加1块钱就是双蛋。肠粉铺是夫妻俩开的,阿叔做肠粉,阿姨招呼来吃的客,收钱找钱,从阿叔手里接过肠粉,浇上汤汁,给等着的人送过去。阿叔高瘦,围裙宽松地系在身上,溅上白色的粉浆,手不停地换着面前的几层簸箕盘,阿姨跟阿叔两人脸都瘦长,微微黄黑,很有夫妻相。
79栋的大人们都是差不多的时间搬进来的,都是差不多的时间生的孩子。
妈说,小悦现在已经能吃辣了,家里人吃,她就跟着吃。小悦住二楼,比我大几个月,画画厉害,吃辣也厉害。我不会吃辣。
正上方住着潼潼。潼潼爸妈又吵架了,忘了是谁说了一句。头顶的天花板被踩出咚咚声,一串男的女的厚的尖的声音大大咧咧从楼上的窗户里走出来、走下来,走进我们家的窗户里。潼潼外公爱画马,也爱买彩票,每天都买20块钱的,但没听说过中了大奖。潼潼阿婆煲的胡萝卜玉米龙骨汤好香,喝起来有点苦,可能是药草味。潼潼没拿稳,我看着他晃出来的那片,有点失神。
梓涵妈妈怀了个妹妹,整栋楼都知道了。阿姨一直想要个女儿,因为梓涵太闹。阿姨说昨晚听到我弹古筝了,妹妹在我的古筝曲里入眠,我弹的是《渔舟唱晚》,妹妹应该做了个好梦。
七楼的骏骏好怪,总是一个人待在上面看书,不爱下来跟我们玩。妈说他是天才,我们说他是怪胎。他好像又拿了奥数比赛特等奖。
对楼住着炳志,他爸每次回家,都在楼下大喊一声“儿啊”,让炳志给他开楼下的大门。他家厅堂悬着个黑色的拳击沙袋,不知道是他打还是他爸打。炳志喜欢小悦,我们都说。
小悦家买了新房子,先搬走了。我在这里住到了十二岁,要上初中,也搬了出去。不久后听说,北屋村要拆迁,后来大家应该也都陆陆续续搬出去了。
深圳有座山,叫笔架山,山脚下曾经有个村,叫北屋村。
那里有着我的十年。
十年
我好像在某一刻又触碰到了我的灵魂。它并不是那么空,它从来都不空。
79栋的人来自各地,四川的、湖南的、安徽的都有,但都说着普通话。
这座城也是。
多愁善感的一朵说她从北京坐飞机回家,飞到城市上空时,看到夜里明黄的深圳的灯、车尾的霓虹,想哭。
我说,你真矫情。
这座城有时候很挤,要机场那么大的地铁站,才托得起岗厦的七点。但也有时候很空,过年的时候,我躺在公园的草坪上,一座城的太阳我一个人晒。
这里有爸、妈、妹,有北屋村,有我的第一个十年。这里有东门,有湖北话、东北话、广东话,也有普通话,有我的第二个十年。
北京,中国的首都啊!外公知道我要去北京上大学,高兴全写在脸上。外公好像有首都情结,喜欢西安,喜欢南京,喜欢洛阳,当然,还是更喜欢北京。
我会闯入一个新的世界,我正在闯入一个新的世界。
你是哪儿的人啊?我又一次听到这句话。
我来自深圳。
南山南,北海北,那里有我的故乡……
我会带着它一起,走入我的第三个十年。